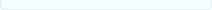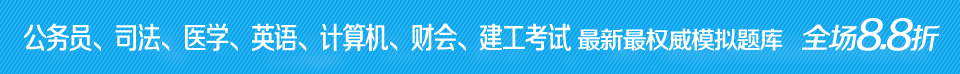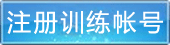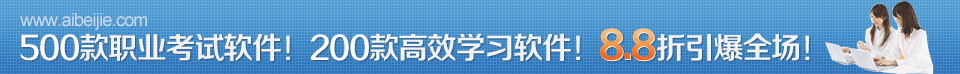- 掃碼訪問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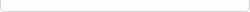
5,998,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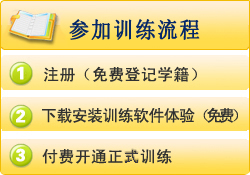
情緒會影響記憶嗎?
人的情緒變化對記憶力會有什么影響呢?這是不少心理學家正在探索的問題。
1981年2月,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G. 波衛爾在《美國心理學家》雜志上介紹了他的一項研究成果。波衛爾發現,記憶力與人的情緒狀態密切相關。人們要從記憶深處回憶某一事物,常常取決于回憶者的心情是否與這一事物發生時的心情相一致。
波衛爾做了這樣一個實驗。他讓斯坦福大學的六個學生小組參加一次情緒與記憶測驗。測驗中,要求學生在催眠狀態中回想親身經歷過的“愉快歡樂”的情景,這種回想因人而異,有的是在足球賽上贏球得分的回憶,有的是一次激動人心的海濱馳馬,總之,使自己置身于歡樂的情緒之中。然后,讓學生在歡樂情緒中學習一張列成16項的互不相關的單詞表。完成后,一部分學生繼續在歡樂情緒中學習第二張單詞表,另一部分學生則用同樣的想象法進入憂傷的情緒,在憂傷的情緒中學習新的單詞表。最后對所有學生進行回憶第一張單詞表的測驗。
實驗結果表明,如果回憶對學生的情緒與最初學習單詞表時的情緒相同,則對單詞表的回憶成績較好。例如,記憶是在學生心情歡樂時獲得的,如果在歡樂狀態中進行回憶,大都比較容易回想起來。但如果在憂傷的心情下回憶,回憶成績明顯較差。波衛爾是這樣解釋實驗結果的:這好比兩種精神狀態各自構成自己的庫房,其中存放著記憶的檔案,只有返回到最初存放某事物的那個庫房或情緒狀態,才能重新取得它的記憶檔案。波衛爾還發現,人們對于童年經歷和個人經歷的回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回憶時的情緒,快活的人所記起的愉快事情要比不愉快的事情多得多。發怒的人常對不帶感情色彩的言語產生憤怒的聯想,動輒對別人吹毛求疵。人們在讀小說時,如果心情憂傷,常會過多注意文中纏綿悱惻的章節,更多地同情那些悲悲戚戚的角色。
根據這些研究,波衛爾提出了記憶與情緒相關效應的假說。這一假說得到不少研究者的支持。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H·魏某和特納等人測試了躁狂和抑郁癥狀交替出現的精神病人的記憶力,也發現病人的情感狀態變化越大,就越容易忘掉幾天前學過的單詞。病人從記憶檔案中尋找有關信息的能力,與這些信息在記憶時的情緒密切相關。在某些能改變精神狀態的藥物如大麻、氨基丙苯、鹽酸氯丙嗪的影響下所獲得的記憶,只有在再次服用這些藥物時才能重溫。
然而,也有不少研究者不同意波衛爾算假說。英國劍橋醫學研究中心的A·巴德萊指出,記憶和回憶時所處的環境有一定關系,波衛爾等人強調情緒和記憶的關系,其實所謂“情緒”不過是環境條件的一部分罷了。其他的環境條件同樣會影響記憶。例如,讓潛水員穿上全套潛水服,在水下10英尺處學習一些互不相關的單詞,以后,只要他們處在同樣的水下環境,就能記憶起較多所學的單詞。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E·洛塔斯也不同意記憶和情緒相關效應的假說。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洛塔斯做了這樣一個實驗:讓受試的大學生看一部情節緊張、使人提心吊膽的兇殺電影,看完后過一段時間,讓受試者回憶電影中的情景和各自的情緒反應。洛塔斯說,我們沒有找到情緒狀態對記憶的效應,促發現高度的緊張焦慮有可能縮短注意時間、妨礙人們的記憶。洛塔斯認為:記憶是“活”的,會生長。人們每次回憶一件事,記憶都在起變化,記憶會從后來的事情中,從增長的認識中,從新的環境條件和情緒狀態中吸取新的含義。正是這些因素使
得目睹同一罪行的大學生產生不同的印象,造成矛盾的記憶。不能簡單地認為記憶和情緒相關。
情緒對記憶到底有沒有影響?研究者們正在進一步探索。記憶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在實驗室里研究局限很大,而在實驗中如何誘發一 定的情緒,研究者們的意見也頗不相同。這些都是研究中的障礙。情緒和記憶的關系,至今仍然是心理學研究中引起爭議的謎。
- 掌握速讀記憶,倍增學習效率! 即刻開始改變一生的速讀記憶訓練>>>
- (精英特版權所有,轉載時敬請保留以下信息:文章來源--精英特速讀記憶訓練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