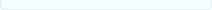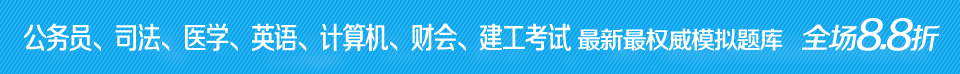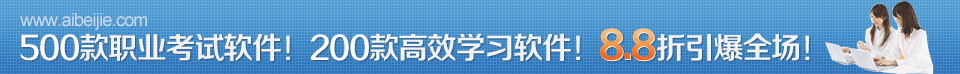其一 ,對(duì)于書籍的讀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讀“書”,一是讀“人”。正像教書也可以分成教“書”和教“學(xué)”一樣。讀“書”是以我為主,我尋材料供我用,和查考辭書類書的目的一樣;所以讀的書,也無所謂好壞,凡可以供我利用的都要讀。這正是寫卡片抄材料的記問之學(xué),學(xué)得好時(shí),便是淹博。讀“人”卻不然:讀一人的著作,想見其為人,于是尊之為師,敬之如友,研其思想,學(xué)其品行,擇善而從,不善則改,所注意的是見解,所學(xué)習(xí)的是做人,不嫌狹隘,但求貫通。這樣讀書,結(jié)果也許只精讀一部全集,但確可以受用終身。讀“書”能博足以炫人,所失在淺;讀“人”而精足以立己,所弊在陋。此外的讀書,若不是當(dāng)課本學(xué)技術(shù),就只能算是消遣而已。
其二,“學(xué)以致用”是句老話,“不要讀死書”是句新話;但從學(xué)問的本身說來,無所謂有用無用;而從學(xué)的人這方面說來,只要真學(xué)就真有用,就是說,至少所學(xué)直接對(duì)己間接對(duì)人都有影響;所以,如果我們不把“用”的范圍定得太偏狹,在學(xué)習(xí)的時(shí)候,我們就該事先注意這學(xué)習(xí)所應(yīng)有的結(jié)果。這樣便不能生吞活剝的讀書,給人家當(dāng)收音機(jī);學(xué)的經(jīng)過也就應(yīng)當(dāng)大致分做:學(xué)——思——行;打個(gè)比方說:吸收——消化——營養(yǎng)。
其三,抽象地論讀什么書,似乎無益,其實(shí)也很有幫助。讀專書,專讀書,都已近于老生常談了,實(shí)際上奉行的人還是很少。讀書人大半還是喜歡東抄西撮雜湊起來的書,只求便捷,不怕膚淺,又喜歡
廣博而不肯專精;這都是不能牢記著上兩條原則的結(jié)果。還有一條原則也很重要,便是多讀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書。我們往往翻開一本書后,一看句句都是自己心中要說的話,于是非常痛快,佩服,很高興地看下去,以為這是正對(duì)自己胃口的好書。結(jié)果卻往往是一無所得,既有進(jìn)步也很少;因?yàn)闀幸庖姡约杭仍谧x書之前便有,那么讀了之后,自然也不過是更堅(jiān)信或更豐富而已。惟有讀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書,可以使自己瞿然一驚,然后以敵人的態(tài)度去觀察這本書的意見。結(jié)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見解不對(duì),從此便更進(jìn)一 步;若自己攻破了書中的理論,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論敵的沖鋒,無形中也加強(qiáng)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正合吾意”的書愈多讀,愈無進(jìn)步,愈容易流入偏狹;遠(yuǎn)不如多讀幾部不合吾意的書。但這樣讀書也有兩個(gè)先決條件:第一是要能批判地讀書,有自己存在,不為書所囿;第二是有所為而讀書,不要視同看看小說之類的
消遣。
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字止默,筆名辛竹,安徽壽縣人,中國著名文學(xué)家,翻譯家,梵學(xué)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與季羨林、陳玉龍并稱“北大三支筆”,和季羨林、張中行、鄧廣銘一起被稱為“未名四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