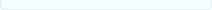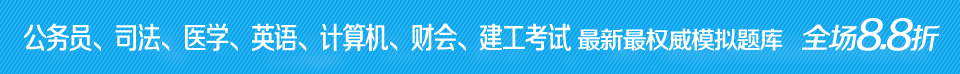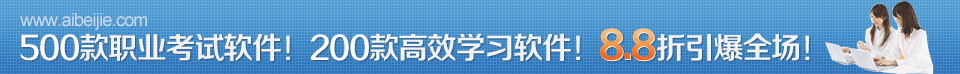我們確定你已經(jīng)看出來(lái)了,你在讀一本書(shū)時(shí)要提出的四個(gè)問(wèn)題,到了讀實(shí)用性的書(shū)時(shí)有了一點(diǎn)變化,我們就來(lái)說(shuō)明一下這些變化。
第一個(gè)問(wèn)題:這本書(shū)是在談些什么?并沒(méi)有改變多少。因?yàn)橐槐緦?shí)用的書(shū)是論說(shuō)性的,仍然有必要回答這個(gè)問(wèn)題,并作出這本書(shū)的大綱架構(gòu)。
然而,雖然讀任何書(shū)都得想辦法找出一個(gè)作者的問(wèn)題是什么(規(guī)則四涵蓋這一點(diǎn)),不過(guò)在讀實(shí)用性的書(shū)時(shí),格外是一個(gè)決定性的關(guān)鍵。我們說(shuō)過(guò),你一定要了解作者的目的是什么。換句話說(shuō),你一定要知道他想解決的問(wèn)題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他想要做些什么。因?yàn)樵趯?shí)用性的書(shū)中,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就等于是知道他想要你做的是什么,這當(dāng)然是非常重要的事了。
第二個(gè)問(wèn)題的變化也不大。為了要能回答關(guān)于這本書(shū)的意義或內(nèi)容,你仍然要能夠找出作者的共識(shí)、
主旨與論述。但是,這雖然是第二階段最后的閱讀工作(規(guī)則八),現(xiàn)在卻顯得更重要了。你還記得規(guī)則八要你說(shuō)出哪些是作者已經(jīng)解決的問(wèn)題,哪些是還沒(méi)有解決的問(wèn)題。在閱讀實(shí)用性的書(shū)籍時(shí),這個(gè)規(guī)則就有變化了,你要發(fā)現(xiàn)并了解作者所建議的、達(dá)到他目標(biāo)的方法。
換句話說(shuō),在閱讀實(shí)用性書(shū)時(shí),如果規(guī)則四調(diào)整為:“找出作者想要你做什么。”規(guī)則八就該調(diào)整為:“了解他要你這么做的目的。”
第三個(gè)問(wèn)題:內(nèi)容真實(shí)嗎?比前兩個(gè)改變得更多了。在理論性作品中,當(dāng)你根據(jù)自己的知識(shí)來(lái)比較作者對(duì)事物的描繪與說(shuō)明時(shí),這個(gè)問(wèn)題的答案便出來(lái)了。如果這本書(shū)所描述的大致與你個(gè)人的體驗(yàn)相似時(shí),你就必須承認(rèn)那是真實(shí)的,或至少部分是真實(shí)的。
實(shí)用性的書(shū),雖然也會(huì)與真實(shí)作比較,但最主要的卻是你能不能接受作者的宗旨—他最終的目標(biāo),加上他建議的達(dá)成目標(biāo)的方法—這要看你認(rèn)為追求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才是最好的追求方法而定。
第四個(gè)問(wèn)題:這本書(shū)與我何干?可說(shuō)全部改變了。如果在閱讀一本理論性的書(shū)之后,你對(duì)那個(gè)主題的觀點(diǎn)多少有點(diǎn)變化了,你對(duì)一般事物的看法也就會(huì)多少有些調(diào)整。(如果你并不覺(jué)得需要調(diào)整,可能你并沒(méi)有從那本書(shū)中學(xué)到什么。)但是這樣的調(diào)整并不是驚天動(dòng)地的改變,畢竟,這些調(diào)整并不一定需要你探取行動(dòng)。
贊同一本實(shí)用性的書(shū),卻確實(shí)需要你采取行動(dòng)。如果你被作者說(shuō)服了,他所提議的結(jié)論是有價(jià)值的,甚至進(jìn)一步相信他的方法真的能達(dá)到目的,那就很難拒絕作者對(duì)你的要求了,你會(huì)照著作者希望你做的方式來(lái)行動(dòng)。
當(dāng)然,我們知道這種情形并不一定會(huì)發(fā)生,但我們希望你了解的是,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那就表示雖然這個(gè)讀者表面上同意了作者的結(jié)論,也接受了他提出來(lái)的方法,但是實(shí)際上并沒(méi)有同意,也沒(méi)有接受;如果他真的都同意也接受了,他沒(méi)有理由不采取行動(dòng)。
我們用一個(gè)例子來(lái)說(shuō)明一下。如果讀完本書(shū)的第二部分,你(1)同意分析閱讀是值得做的。(2)接受這些
閱讀規(guī)則,當(dāng)作是達(dá)到目標(biāo)的基本要件,你會(huì)像我們現(xiàn)在所說(shuō)的一樣,開(kāi)始照著閱讀起來(lái)。如果你沒(méi)有這么做,可能并不是你偷懶或太累了,而是你并不真的同意(1)或(2)。
在這個(gè)論述中有一個(gè)明顯的例外,譬如你讀了一篇文章,是關(guān)于如何做巧克力慕斯的,你喜歡巧克力慕斯,也贊同這個(gè)作者的結(jié)論是對(duì)的,你也接受了這個(gè)作者所建議的達(dá)到目標(biāo)的方法—他的食譜,但你是男性讀者,從不進(jìn)廚房,也沒(méi)做過(guò)慕斯,在這樣的情況中,我們的觀點(diǎn)是否就不成立了?
并不盡然!這正好顯示出我們應(yīng)該要提到的,區(qū)分各種類(lèi)型實(shí)用書(shū)的重要性。某些作者提出的結(jié)論是很通用或一般性的—可供所有的人類(lèi)使用—另外一些作者的結(jié)論卻只有少數(shù)人能運(yùn)用。
如果結(jié)論是通用的—譬如像本書(shū),所談的是使所有人都能閱讀得更好,而不是只有少數(shù)人—那么我們所討論的便適用于每位讀者;如果結(jié)論是經(jīng)過(guò)篩選的,只適用于某個(gè)階層的人,那么讀者便要決定他是否屬于那個(gè)階層了;如果他屬于那個(gè)階層,這些內(nèi)容就適合他應(yīng)用,他多少也有義務(wù)照作者的建議采取行動(dòng);如果他不屬于這個(gè)階層,他可能就沒(méi)有這樣的義務(wù)。
我們說(shuō)“可能沒(méi)有這樣的義務(wù)”,是因?yàn)楹芸赡苓@位讀者只是被自己愚弄了,或誤解了他自己的動(dòng)機(jī),而認(rèn)為自己并不屬于那個(gè)結(jié)論所牽涉的階層。以巧克力慕斯的例子來(lái)說(shuō),他不采取行動(dòng),可能是表示:雖然慕斯是很可口的東西,但是別人—或許是他妻子—應(yīng)該做給他吃。
在許多例子中,我們承認(rèn)這個(gè)結(jié)論是可取的,方法也是可行的,但我們卻懶得去做,讓別人去做,我們會(huì)說(shuō),這就算是交待了。當(dāng)然,這個(gè)問(wèn)題主要不是閱讀的,而是心理的問(wèn)題,心理問(wèn)題會(huì)影響我們閱讀實(shí)用性的作品,因此我們?cè)谶@里有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