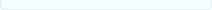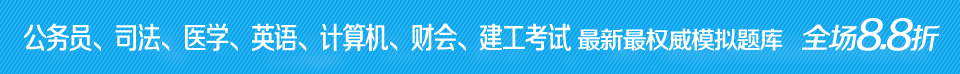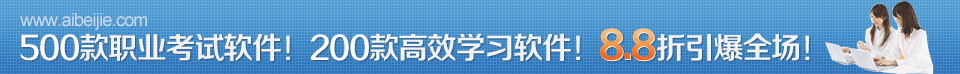導(dǎo)讀:書是拿來讀的,怎么能煮來吃呢?相信大家讀到這個標(biāo)題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其實,說“煮書”只是一個比喻罷了,正如老一輩革命家陶鑄曾經(jīng)所說:“做學(xué)問的功夫,是
細(xì)嚼慢咽的功夫。好比吃飯一樣,要嚼得爛,才好消化,才會對人體有益。
說“煮書”,其實同說“吃書”一樣,只是一個比喻。難道,真把書煮來吃了不成?當(dāng)然,如果真的把書“煮”了,然后吃下肚去,卻也是有很多好處的。作家茹志鵑在書齋里“煮書”,大概就是這樣策劃的。
老一輩革命家陶鑄曾經(jīng)說過這樣一段話:“做學(xué)問的功夫,是細(xì)嚼慢咽的功夫。好比吃飯一樣,要嚼得爛,才好消化,才會對人體有益。”所以有人就把這樣的讀書叫做“吃書”。比如數(shù)學(xué)家
張廣厚的夫人,就曾經(jīng)這樣打趣張廣厚:“這哪叫念書啊,簡直像吃書。”為什么說張廣厚念書“像吃書”呢?因為孔夫子“韋編三絕”,張廣厚呢,讀一篇20多頁的關(guān)于虧值的論文,反反復(fù)復(fù),半年多的時間里,竟把那書邊翻成了黑邊。就這樣描述張廣厚“吃書”,其實意猶未盡。看看,他同詩人臧克家說的“以求吃盡書中味”不也是在同一水平線的嗎?豈止是“吃”,原來已經(jīng)進(jìn)入“品味”的境界了。詩人“吃書”品味,科學(xué)家“吃書”,不也從中品出了“科學(xué)技術(shù)也是生產(chǎn)力”的滋味來嗎?這樣的“吃書”,都是要“煮”了來吃的呀!而且還要是“煮熟”了,不是“一鍋夾生飯”,這樣才有利消化,有利吸收。所以宋代理學(xué)家朱熹說:“讀書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是味也。”
20世紀(jì)80年代的一天,黃宗英應(yīng)邀到四川大學(xué)講學(xué)。她對師生們說:“我一走進(jìn)校園,看見同學(xué)們在明亮的教室里讀書,就饞得慌,比餓著肚子看別人吃香甜麻辣的四川小吃還饞得慌哩!”所以,高爾基“撲在書籍上,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一樣”。這種“餓相”,在杰克.倫敦,他的一位朋友是這樣子描述的:“他捧起一本書,像一頭餓狼,把牙齒沒進(jìn)書的咽喉,兇猛地舔盡它的血,吞掉它的肉,咬碎它的骨頭,直到那本書的所有纖維和筋肉成為他的一部分。”這樣的過屠城而大嚼,打精神牙祭,真是一件大快朵頤的事情。這種狀況,有的是因為饑餓,有的是因為饑渴。當(dāng)然,“饑”就是“餓”,所以咱們就把如此這番狀況概括地表述為:
如饑似渴。
解決了饑渴和消化吸收的問題,另一類的“吃書”,就更上一層樓了。莎士比亞講:“書籍是全人類的營養(yǎng)品。”豈止是充饑解渴之類!書籍是精神生活的養(yǎng)料,叫做“精神食糧”。不知同什么比,有的又把它叫做“精神佳肴”。就算“充饑”吧,宋代學(xué)者尤袤也說是:“饑,讀之以當(dāng)肉。”真是英雄所見,作家賈’平凹在《好讀書》一文中也這樣談到:“讀書讀得了一點新知,幾日不吃肉滿口中仍是余香。”嗅嗅,這哪里只是“充饑”、“解渴”的營生呢?當(dāng)然,賈平凹讀書早已是越過了溫飽的界線而步入了小康社會的。那些還沒有解決溫飽的老百姓,就曾,經(jīng)多次問過一些讀書人:“看書就能看飽了?”所以在他們看來:“書是不能當(dāng)飯吃的。”至于“書中自有”什么什么,那不是人人都看得見的。但是,也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飯可以不吃,書則是不可不看。這些讀書人啊,硬是要把書拿來當(dāng)飯吃。
陳毅元帥還在家鄉(xiāng)的時候,有一年中秋節(jié)走親戚。在親戚家,陳毅發(fā)現(xiàn)了一本“好書”,于是他就獨個兒地讀起書來。開飯了,可是怎么催他都舍不得把書放下,于是就只好把過中秋的糍粑和糖給他送到面前。這樣,陳毅一邊看書,一邊吃著糍粑。隔了一會兒,親戚家又給他送來面條,卻見陳毅滿嘴的墨,原來卻是把應(yīng)該蘸著糖吃的糍粑伸到硯臺里蘸上墨汁吃了。有形容說是書讀少了其表現(xiàn)就是“肚子里墨水少了”,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典故。說到引經(jīng)據(jù)典,“《漢書》下酒”要算著名的一例。北宋詩人蘇舜欽,在他岳父家居住的時候,每晚都要飲酒一斗。不過我猜想呵,那時的酒可能沒有現(xiàn)在的五六十度的高度。但是在詩人的岳父看來,這女婿的酒量也是十分的驚人。而且,每晚一斗,也未免有些“貪杯”了吧。
于是,老人有了探個究竟的念頭。那一晚,他悄悄地來到女婿的屋子外面,窺窗而望,耳畔也正聽得蘇舜欽那津津有味地朗讀《漢書·張子房傳》的聲音。當(dāng)彼之時,蘇舜欽正讀到張良狙擊秦始皇,誤中副東,“惜乎擊之不中!”詩人拍扼腕,隨手端起酒盅,一飲而盡;又讀到張良對高祖說:“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拍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又滿飲一盅……岳父見狀,喜上心頭,自言道:“如此下酒,一斗也不算多。”看來,這老人最初是有點吝嗇他的“好酒”呢。
不過,不論什么書下酒,也不論什么度數(shù)的酒,總之還是有點考酒量。于是,讀書飲酒,大致就有了這樣三態(tài):小醉大醉和半醉。據(jù)描述,小醉的讀書人,每有會意,即喜上眉頭,逢人夸耀,以為談資,還生吞活剝地背上幾段,于是乎曰:老先生醉也。大醉的讀書人有如不知節(jié)制的酒鬼,貪杯成癮也還罷了,令人討厭的是那副醉生夢死的醉相,和那不時嘔吐的穢物:什么某某某的書我最愛,讀得心坎里面熱乎乎……讀書,這般樣地“下酒”,是為不勝酒力了。據(jù)說,讀書下酒,良好的狀態(tài)是半醉。既入得去,也出得來。有點醉了,可流連其間;留一半清醒,還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世間道理。似醉非醉,這便是進(jìn)入到讀書的一種境界了。也好比吃飯,既要吃飽,又不能過飽,健康的吃法即是“半飽”。因為讀書“過飽”,也有因噎廢食的。這種情況,又多是因為“偏食”引起的。所以讀書,既要“撲在面包上”,也還要“撲在大米上、蔬菜上”等等,別以為高爾基就只是“吃面包”長大的。
報人曾伯炎先生講過一個故事:他認(rèn)識一位中年作家,既專又博,且博得使他吃驚。原來是該作家時不時備好一桌筵席,請來學(xué)者、教授談天。這樣,人家研究一生的學(xué)問,他用一餐飯便拿走了。這當(dāng)然只是個案。至于要“拿”人家的學(xué)問,途徑多的是。亦誠如肖伯納所言,蘋果互相交換了還是一個,思想交換了就都得到了兩個思想,不僅不貶值還會增值。這其間,皆需“尚能飯否?”
“讀書如吃飯”,越說還真是越象那么回事了。因此,就有人提出了“善吃”的方法。清代詩人袁枚的處方是:“善吃者長精神,不善吃者生癡瘤。”英國哲學(xué)家培根的實驗報告是:“有些書可以嘗一嘗,有些書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幾部書則需要咀嚼消化。”讀書,又有點不像是“吃飯”了。西漢學(xué)者劉向說:“書擾藥,善讀之,可以醫(yī)愚。”希臘諺浯中也有:“書籍是心靈的良藥。”難怪讀書需要“煮”,這在咱們服中藥的,還是需要“熬”呢。
或問:真有“吃書”這檔子事?據(jù)《世說新語》記載,有一個叫郝隆的人,七月七日那天,在屋外仰面躺著曬太陽。別人問他干什么,答曰:“我曬書。”書在什么地方?清代文學(xué)家蒲松齡拍拍肚皮,回答問他這問題的官人洪家軍說:我的書都裝在這里啦。洪家軍雖然做了官,但是肚皮里面卻沒裝多少書,然而洪家軍卻要附庸風(fēng)雅,還擔(dān)心別人不知道,于是就把書搬了出來曬太陽。蒲松齡在仕途上不好與洪官人比,但是要比讀的書,洪官人就汗顏了。這以后,洪家軍再也不敢曬書了。據(jù)說,這樣的事,康熙帝在出巡途經(jīng)浙江省嘉興市王店鎮(zhèn)(今名)的時候,也曾碰到一長者
袒腹曬書。說是一肚皮書派不上用場,擔(dān)心發(fā)霉腐爛變質(zhì),于是給它們曬曬太陽。真是太形象了!古話說得好:“腹有詩書氣自華。”那么,還不趕快吃,干嘛呢?
真吃呀?真吃!唐代的張籍已經(jīng)做了示范:籍取杜工部一個包書的布套,焚燒了,取其灰燼,輔以膏蜜,吃了。張籍還說了:“令吾肝腸從此改易!”那么,不知是不是這以后他才寫出了《節(jié)婦吟》的?恕我無力考證了。(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