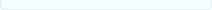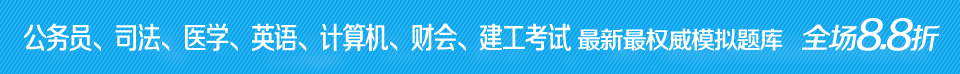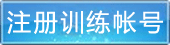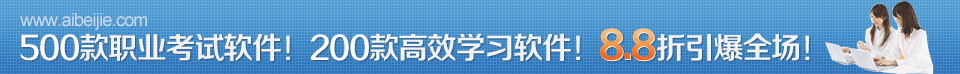- 掃碼訪問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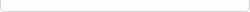
5,999,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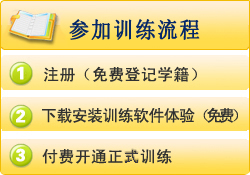
快速閱讀相關:“小一碼”讓閱讀更愉悅更輕松
很多人會承認閱讀的地位,但不是每個人都覺得閱讀是件愉悅的事情,也許是因為繁忙的工作與厚厚的書本之間的矛盾,也許是覺得書中層層疊疊的字堆起來是那么地枯燥,缺乏讓人耳目一新的字句,棄之可惜,讀之無味;或是覺得千百年來沒怎么變化的紙質書,沒有手中時尚輕巧的電子書稱心。而現在,“小一碼”的圖書悄然進入我們的視線,“精致”就是它的代名詞,也許有了它,我們在快速閱讀時能感到不一樣的輕松和愉悅。
看紙質書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我們的地鐵中少有捧書閱讀的現象,在感嘆的同時,我們是否想過,設計一種符合閱讀習慣、手感超好的紙質書,讓閱讀本身變得更舒服、更輕松?
邂逅“小一碼”圖書
作者走進這家書屋,進門左開間有一個書架。
如果只是一眼掃過,大概不會發現其中的特別:書架的中間三行,碼放著一系列“小一碼”的最新出版的書。與通常不同,它們不是單純按照內容碼放的,這些書里,涉及散文、小說、詩歌、哲學……之所以被集中到此,原因是它們的個頭——如果在它們邊上放一本主流開本的書,“小一碼”便一目了然——3/4的體積,3/4-1/2的重量。
這讓人聯想起日本書店的“文庫本”書架。
在日本,專門為小一碼的文庫本設立的書架非常普遍,家具店里,甚至有專門為文庫本設計的書籍隔板。“文庫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日本的巖波書店為了對抗市場上豪華昂貴的經典巨著,推動文化傳播,推出了一系列小巧、價格便宜的文庫本。巖波書店的理想完美地達成了——文庫本成為日本圖書出版業的重要勢力,日本人在地鐵電車上閱讀的習慣從明治維新時期一直保持至今,與文庫本有莫大關系。
與那三行“小一碼”書對照的,是書店中的占據主導地位的大開本書。
店主回憶上世紀九十年代她剛入行時,“書架遠不是現在的高度。但近十年,越來越多的大開本出現,就只能定制新的書架。”
大開本的席卷,背后必然各種因素交雜,比如更大的利潤空間、碼放時的搶眼程度,以及購書者的消費心理。情形的演變程度,甚至到了讓人啼笑皆非的程度:精致厚實的大開本,翻開,留白是內容的一倍乃至幾倍。
但是,我們真的需要那么多“與國際接軌”的大書嗎?
紙質書的新對手——電子書
不得不提到電子書。
數字化閱讀這一全球的閱讀趨勢,在過去的幾年里,給傳統的紙質書市場帶來了極大的恐慌,并且勢力還在蔓延。
數字化閱讀在短短六七年里異軍突起,全球網絡化是重要的生態背景,但其強悍同樣建立在,除了大容量、越來越輕巧、易于攜帶的體積,還有它不斷“接近紙質書”的閱讀體驗。
有人這樣定義電子書:“它從一開始就是一本書”,而它的最終目標則是“從你的手中消失”。這一“消失”,指的就是讓電子書使用者們忘記自己盯著的只是一塊N英寸屏幕。
當“紙質書擁有紙所不能代替的質感”與“紙書的重量和有限容量”之間的爭執多年后,電子書在“消失”的路上飛奔,而紙質書的設計,似乎始終停留在對外觀的追求上。
從某種意義上說,紙質書的設計,與電子書并無二致,同樣是內容的載體。因此,我們不禁想,紙質書是否也能在紙張質感的基礎上,讓閱讀變得更舒適、更愉悅、更不增加閱讀者的負擔,或者換一個詞:更人性?
體驗精致
讓我們拋開書的內容,直接來看書的設計本身——隨手選擇一本小一號圖書用來作為標本:
書比正常的32開本小兩個尺碼,11.5×16.6,差不多是手掌的長寬度——一手就能掌握,但有沒有窄小到逼仄的程度。事實上,這種開本,在中國的古籍中并不少見。
書的封面是棉麻的柔韌質地——此后,我們將看到它的特別所在。
拿起書,它的重量傳遞到你手中,只有同類書的3/4-1/2。
把書脊放在手掌中,打開,淺黃色的內頁光澤柔和,因此書的字體雖然不大,但依舊讓眼睛愉悅,另一個不累眼睛的原因是書的行間距,疏朗程度遠離了傻大的字體帶來的壓迫感,卻又沒有不知所謂的大片留白。這一設計另一合理之處在于,開本盡管變小,書的內容量依舊得到保證:330頁中,包括了近80頁的圖片和說明,依舊能容納20萬字。
翻頁。第1頁、第101頁或者第301頁,內頁都溫順地躺倒,另一只手基本只需要翻頁,而不用費心摁住不斷企圖合攏的書頁。
合攏書,把它放進隨身的包里,封面的特別所在顯現出來:盡管是平裝本,它卻擁有著精裝的優點:不會卷角,無論是內頁還是封面;與此同時,又避免了精裝本對承重能力的考驗。
設計在這里,不是為了張揚設計本身或者吸引消費者的眼球,而是為了愉悅的閱讀體驗。
遺憾的是,這一類型的書寥寥無幾。
盡管也漸漸有出版社開始重新關注“小一碼”書,但這些讀本要真正成為風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反過來想,這樣的書架已經出現,這樣的形式已成趨勢。
影響我們閱讀效率的因素很多,得人心者得天下,不管是電子書,還是小一號書,只要它能讓我們的閱讀帶加輕松,那就是極好的。
精英特速讀記憶訓練網總編輯
- 掌握速讀記憶,倍增學習效率! 即刻開始改變一生的速讀記憶訓練>>>
- (精英特版權所有,轉載時敬請保留以下信息:文章來源--精英特速讀記憶訓練網)